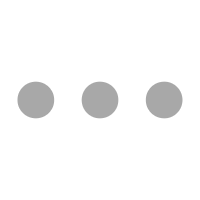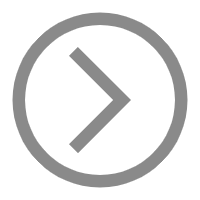早在1963年,Paul Mandel等发表了对PARP酶活性的描述报道,1964年Pierre Chambon等人正式发现PARP酶。PARP酶催化PAR修饰介导的DNA单链损伤修复,以及PARP酶与DNA紧密结合不解离导致的细胞毒性,这两种生物学性质被用于指导PARP抑制剂的开发,成为PARP抑制剂的直接作用机制。从理论上来说,化疗和放疗都会产生大量的DNA损伤,在此基础上使用PARP抑制剂应当能增加化疗药物或放疗的疗效。然而事与愿违,10年间研究者们始终未能证实PARP抑制剂的疗效。 直到2005年《自然》(Nature)杂志同期发表的两篇文章,两个研究团队分别报道BRCA 突变的肿瘤对PARP抑制剂敏感,这是第一次描述PARP抑制剂与BRCA 基因突变的合成致死效应。随后PARP抑制剂的开发进入精准治疗时期。 4年后,奥拉帕利的一项Ⅰ期临床研究证实其在携带BRCA 突变的卵巢癌等肿瘤的患者中具有显著疗效,并且具有很好的安全性和PK/PD性质,这是第一项PARP抑制剂在BRCA突变人群中的临床试验报道。2010年,奥拉帕利在BRCA突变人群中的疗效在另一项概念验证性Ⅱ期临床研究中得到证实。随后的另一项Ⅰ期研究发现,奥拉帕利的疗效与患者的铂敏感状态和化疗线数有关,铂敏感患者的疗效明显更好,化疗线数越多,可能造成患者对PARP抑制剂耐药性越大。在这项研究中,携带BRCA突变的复发性卵巢癌铂敏感患者对奥拉帕利的ORR高达69%,铂耐药患者为45%,而铂抵抗患者仅23%。这为后续开发铂敏感复发(PSR)卵巢癌适应证提供了证据。 2011年,曾因在Ⅱ期临床研究中表现优异,显示出能显著延长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总生存(OS),而成为明星药物的Iniparib,针对三阴性乳腺癌的Ⅲ期临床宣布失败,未能延长患者的PFS。这项研究的失败,给整个PARP抑制剂的研发造成巨大影响,很多相关研究被关闭,美国Merck甚至停止开发已经进入临床阶段的MK-4827(即后来的尼拉帕利),并转卖给一家小公司。反转出现在2012年,Iniparib被证实并非真正的PARP抑制剂,因为其并不能抑制PARP活性。此时,各公司又重启PARP抑制剂的临床研究,其中奥拉帕利再次处于领跑地位,凭借Study-19研究的卓越成果成为全球第一个上市的PARP抑制剂,2014年分别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(EMA)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(FDA)批准上市。